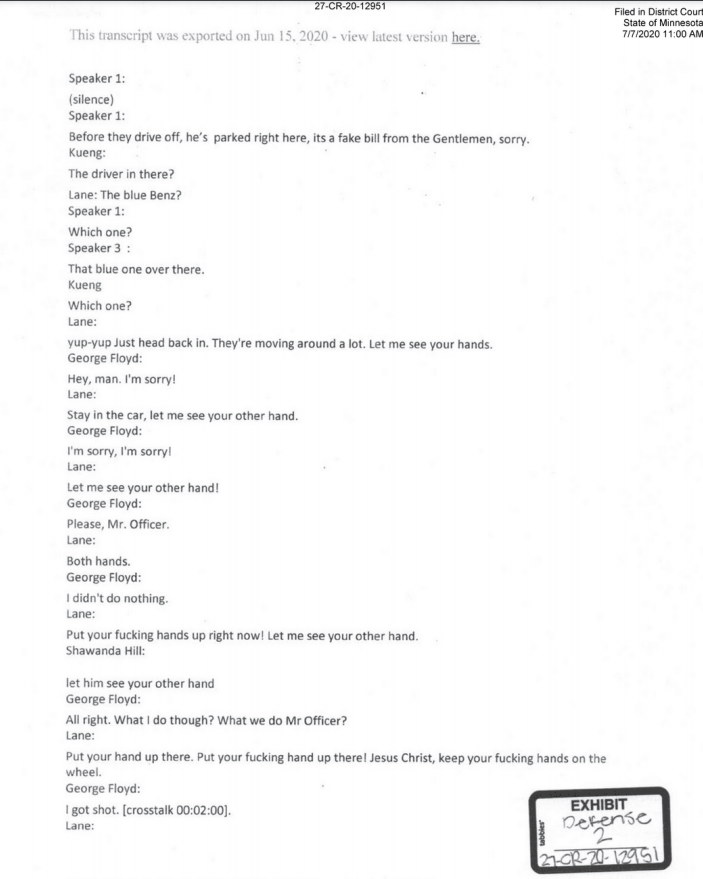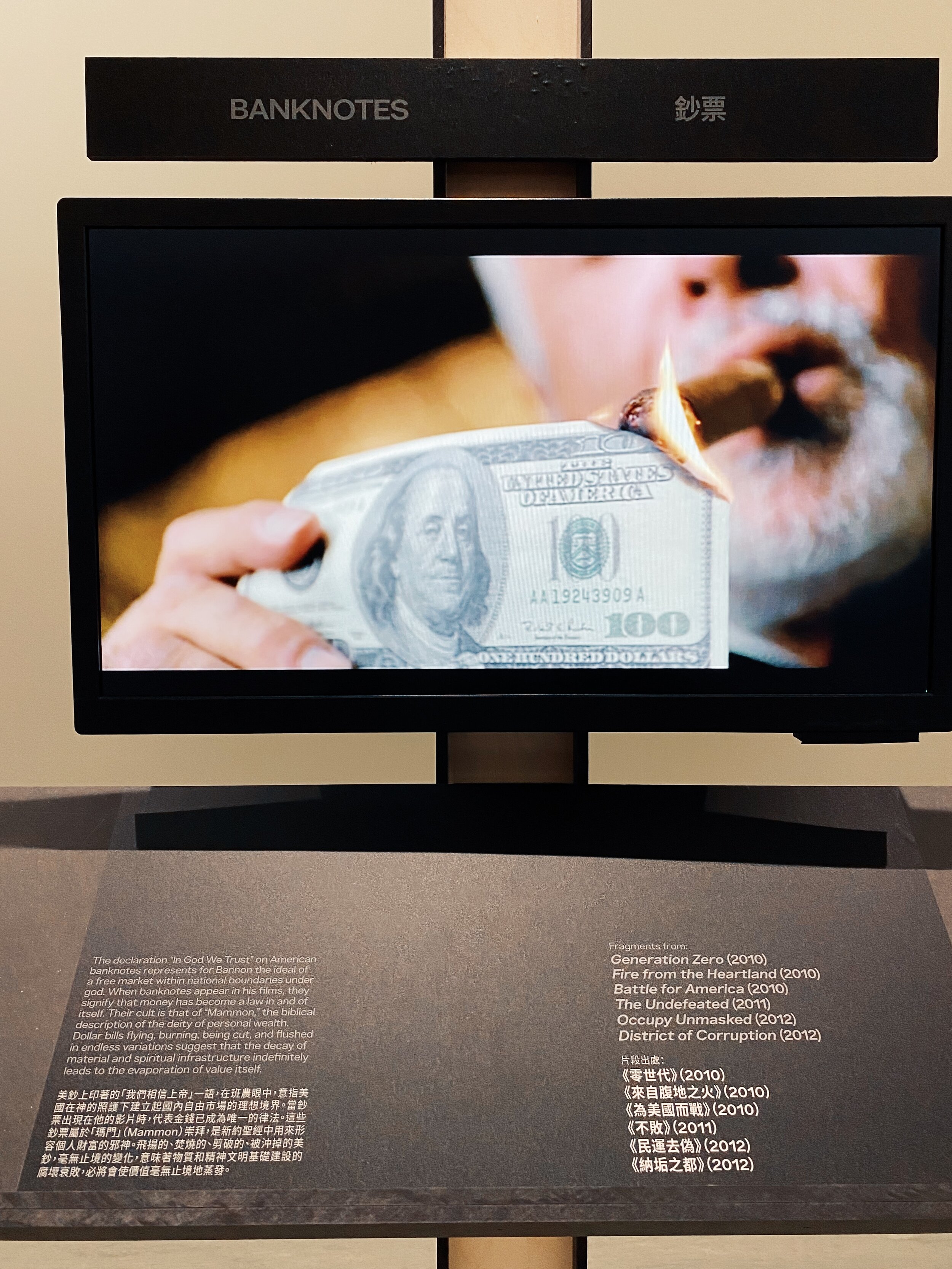好的,那麼我們接下來來請馬景超來聊一下她的學術道路。
馬景超:我自己的研究歷程一直是在哲學領域,但是一直都很劍走偏鋒,越來越往邊緣靠攏。因為在美國哲學界,主流的是分析哲學,而我所在的系是歐陸哲學系。大家應該從名字就能聽出來,歐陸哲學在美國並不是非常主流。我最早對自己的研究方向產生興趣是從女性主義哲學開始的。在本科的時候,我對波伏瓦非常的有興趣,開始閱讀她的著作。
所以在本科的時候,我從波伏瓦入手,然後去從她發散開來,去讀一些她的同時代的人,影響過她或者她影響過的人。也因此申請了歐陸哲學的院系,我的院系對我的研究興趣發展的影響也非常大。我從一開始做女性主義的研究,之後對女性、對性別議題感興趣。在來到美國之後,我比較集中地、系統地接觸了酷兒理論,覺得非常有意思,就開始做一些酷兒理論方面的東西。
之前有段時間跟劉文合作很多,也一起參加過會議。那段時間我也在考慮,不僅是亞裔,更多是東亞的酷兒社群、東亞的同志社群和酷兒理論之間的關系。因為我自己感觸頗深的是,酷兒理論常常被當成是一種比較先進、比較時髦或者是比較洋氣的理論,大家會覺得我們要從英語或者法語去學習這種比較時髦的理論。但同時,我們往往會覺得我們自己是比較無聊的,或者是比較落後的,因為我們還沒有同性婚姻、沒有對某些權利的法律保障等等。
但我自己覺得非常有意思的是,這裡面的先進和落後的關系是如何體現的。我自己當時有一個樸素的想法,我想在這些被大家視為落後的東西裡面,去挖掘一些很酷兒的東西。當時也有寫一些東西,包括關於要去殖民化酷兒理論的一些思考,如何讓酷兒理論不要變成我們只追求西方現在所追求的議題。我認為大家都去追趕美國最新的議題並不意味著我們就成功了 。
但是當我開始寫博士論文以後,我發現自己並不能用一篇博士論文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我現在的博士論文其實說窄也蠻窄的,是從美國的跨性別政治出發,然後從美國跨性別政治的這樣的一個視角,去探討在跨性別政治中我們所預設的自我和身體的一個關系。因為,近兩年來跨性別被放在了美國政治的聚光燈下,我們可以從這里去看看美國社會對於性別的一個焦慮。然後從這種焦慮或者是偏執中,去看美國社會是如何理解性別的;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社會是如何理解自我和身體的。
總的來講,我對於跨國和去殖民的性別研究和酷兒理論一直抱有興趣,將來也希望可以繼續做這方面的研究。
郭婷:好,聽了剛才馬景超的分享,我想到三個我們可以繼續聊的點。一個是對於有些不太瞭解酷兒理論的聽眾,我們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酷兒理論的歷史和它的發展。另外一點就是東西方對立這個問題:把某一些東西的先進性規定為是西方世界的產物,然後把東方的、亞洲的看作是落後的、保守的等等,我覺得大家在很多方面都有這樣的體驗。此外,哲學這個領域對研究酷兒理論和情感研究的發展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先請兩位跟大家介紹一下酷兒理論的歷史跟它的發展好嗎?
劉文:我在高中的時候就去了美國,然後我身處在一個非常異性戀文化的環境之下,就是有高中舞會(prom)的郊區文化(suburban culture)裡面。到了大學以後,我很渴望接觸酷兒的社群,於是我就去了我們學校的酷兒中心(queer center),當時的主任就叫我去念福柯,這也成為了我接觸酷兒理論的一個契機。酷兒理論本身的歷史也非常有趣,在北美70年代、80年代的時候有同性戀解放運動(gay liberation)和女權主義運動,它們對於整個理論的學科建制也作出了貢獻,因此當時有一個研究叫做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研究(gay and lesbian studies)。但這方面研究主要是以歷史性或者社科性質的學術創作為主,他們通常假設同性戀(gay and lesbian,當時還不用queer這個詞)這個主體其實是一直存在於不同歷史之間的。
他們的工作是去挖掘在美國,甚至在不同國家的不同的時期,出現的這種同性欲望(same sex desire)。基於這樣的假設,後來在90年代的時候酷兒理論在比較文學研究領域開始萌生出來,於是它就開始批判比較本質論的對“同性戀主體”的假設。所以酷兒理論一開始就是一個反建制的學科,它認為我們不能用身份認同去定義任何的存在,也不能夠假設同性欲望(same sex desire)這樣的欲望或表現可以被普遍化(universalize);也不認為它可以在不同的脈絡里保持同樣的身份跟表現。相反,此時的酷兒理論聚焦於美國(或者說西方)特定脈絡下同性欲望和同性身份的塑形。
此外,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這些研究連接了精神醫學的發展。其實福柯也說過很多這方面的歷史,因為精神醫學的發展,他們創立了一個可以被病理分析的主體,才會有了同性戀(homosexuality)的概念。所以酷兒理論從發展開始,就是去尋找西方特有的科學跟精神的命題,然後去解構(deconstruct)同性戀概念的起源;酷兒理論不認為同性戀是一個永遠存在的概念,而是一個西方現代性特有的、同性戀跟異性戀的分歧。
林垚:剛才聽劉文介紹了酷兒理論的發展史,這讓我聯想起2018年網飛(Netflix)上有一個劇叫做《姿態》(POSE),是講八九十年代紐約的舞廳文化,就是紐約中下階層的非裔和拉丁裔的酷兒群體組織起的秘密社交網路。為什麼聯想起這部關於少數族裔酷兒的劇呢?一是好像女權理論或者其它性別研究理論,常常在理論發展了幾十年後,就有少數主義群體和學者加入進來,說你們之前的研究都忽略了少數族裔存在,你們都是以白人為模板;女性主義也是一樣的,所以後來才會有交互(intersectionality)研究存在的等等。那麼,在酷兒理論裡面是不是也有種族、跨種族、跨階層慢慢擴展的這個過程?
另一個問題和劉文做的亞裔酷兒研究有關。比如《姿態》這部劇,呈現了中下階層的拉丁裔和非裔的酷兒群體,但是裡面似乎沒有亞裔酷兒的身影。所以我比較想知道亞裔酷兒群體內部的層級是怎樣呈現出來的、亞裔跟其他群體之間的關系。包括像在主流文化里,亞裔美國人男性普遍被去性化,以及女性被作為性癖好(sexual fetish)的觀望對象等等,這些現在大家似乎談得比較多了;但是對於酷兒群體內部怎麼把其中的亞裔酷兒當作性的對象,這方面討論似乎還有待增加?
劉文:我覺得這是一個最近學科發展的重要議題,尤其是種族跟性別的交織。如果回溯到更早一些的時間,他們會回到像殖民時期白人跟黑人生的混血小孩“mulatto”這個概念。其實在19世紀,他們認為白人跟黑人所生的混血小孩(mulatto)是一個無法繁衍也無法生殖的身體和主體。所以很多的酷兒學者就會說,這樣的現象讓我們理解,其實性反常(sexual perversity)或者是無法繁衍的被遺棄的(outcast)性,跟被遺棄的(outcast)種族其實是在同時發展的。
他們會認為同性戀的概念跟種族的分類其實是在同時、尤其是在同一種科學種族主義(scientific racism)的範例(paradigm)下發展起來的,所以我們在講性別的時候是無法將它與種族的階層性分割開來的。這是一個從殖民時期來理解的論述,後來它發展成了一個新的理論,有一個很有名的人類學家大衛·瓦倫丁(David Valentine),寫了本書叫《想象變性:一個類別的人種學》(Imagining Transgender:An Ethnography of a Category),他的田野調查就是關於在90年代紐約,也就是《姿態》這部劇里提到的非常年輕的黑人和拉丁酷兒社群。他發現在他們的認同里,這些人可能會改變身體,比如有些人打荷爾蒙、有人會改變他們的身形等等,但他們不一定會將自己稱為跨性別者(transgender)。
他當時的論證是,在1970年代,當我們看到同性戀從《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里被去掉的同時,一個名為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的疾病被加到手冊中。所以,當美國主流社會開始去病理化同性戀,同性戀所剩下的這種被社會污名化的污點就開始被轉化為跨性別的污點。
有一些比較高階層的,尤其是白人中產階級的同性戀,他們的表現是越來越性別模糊化的(gender confusion)。比如女同性戀並不會像以前一樣很男性化(butch),她們的性別表現可能不會讓你一開始就知道她是圈內人。因為那是一個階層化的過程,同性戀越來越依附於(attach to)一種白人身份的塑形化的過程,她們接受的教育是不囿於既定性別表現的(gender non-conforming)。而性別表現會越來越被階層化跟種族化,那些不合格的種族(尤其是拉丁裔與非裔)會被歸類為不能夠成為體面同性戀的族群。在大衛·瓦倫丁的研究裡面,他發現即使這些人可能會有跨性的表達,但他們並不會使用跨性的標簽。這也是因為當時性別(gender)跟性取向(sexuality)之間存在非常明顯的分割,也讓跨性的概念慢慢地被階層化,如果70~90年代是同性戀的白人化和階層化,那麼到90年代開始,我們又看到另外一波變性人(transgender)被白人化的過程。
所以對於這些處於舞會文化(ball culture)的非裔和拉丁裔青年,他們反而可能會用上男同性戀(gay)這種標簽(label)來描述他們的欲望、他們的社群,或者是他們的性別表現,即使他可能不能夠被完全明確地被分類在囿於既定性別表現(gender conforming)的同性戀角色中。總之他論證說,在北美的社會,即使我們用這種性別的標簽,也擺脫不了其背後的種族含義。
像有一個很有名的紀錄片叫 《陽剛之心》(The Aggressives),它專門記錄了在紐約的、生理性別為女,但是有比較陽剛表現的這一群人。如果在比較白人的社群,她們會被稱為男性化的女同性戀(butch lesbian)。但這個“陽剛”(aggressive)的標簽往往是給比較男性氣質強烈(masculine)的非裔所使用的,因此她們會拒絕女同性戀的標簽,反而她們會認為自己的身份就是一種“陽剛”的表現。所以在美國社會,我們也看到很多不同社群對於自己的種族跟性別、跟欲望交織所產生的不同的身份認同(identity)。
關於你提到的亞裔酷兒,其實在整個運動時期亞裔酷兒都很少被包含在所謂的有色人種酷兒(queer people of color)裡面。這就必須要聯繫到就是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自己的去政治化的歷史,這不是說並沒有亞裔美國人酷兒 (queer Asian American)運動史的存在,而是它真的是一個比較難見到的東西。像在心理學的研究領域中,我們會認為亞裔的家庭是傳統的,對比主流社會來說,亞裔移民家庭對於性的態度是更為保守的。
所以很多的文獻會認為,亞裔酷兒永遠處在一種所謂的雙重約束(double bind)里。如果他們要成為主流的同志,那麼他們就要去融入白人文化,要把自己的認同跟主流白人文化結合在一起,以此建立比較緊密的同志身份認同;而如果他們留在以亞裔移民為主的社群內,他們就會處在一個異性戀規範的社群之中。
我認為這樣的研究其實對於亞裔酷兒是非常不公平的,因為好像他們永遠被卡在兩個主權社會之間,沒有自己的能動性(agency),所以我後來所做的一些研究都是關於亞裔酷兒如何去找到自己的能動性跟社群。這也與我之前做的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研究有關,因為我發現很多的亞裔酷兒運動者,他們並不一定想要參與到以白人同志為主的同志社群內。他們認為那樣的空間和他們的背景以及他們想要做的運動之間是缺少連接的。例如說主流白人要求的一些同志的保障,與許多亞裔酷兒的切身要求之間是缺少聯系的,所以很多的亞裔運動者反而會想要參加以種族為主的訴求運動。像是紐約地區的亞裔對黑人的支持(Asians for Black Lives)運動中,很多亞裔都是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但TA可能不會用酷兒,或者我們所知道的典型議程(agenda)作為TA的政治主體性。所以我們發現有色酷兒(queer of color)社群不會以我們傳統理解的同志運動作為其主要的政治主體性,反而會接觸黑命攸關,或者是反帝國組織(anti-imperialist organizing),並以此作為他們的主要的社群。
林垚:這很有意思,因為我也確實註意到比如說黑人酷兒群體,他們在參與政治時也會依附到黑命攸關運動上面去,他們會說跨性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Trans Lives Matter) 。
然後劉文剛才說的亞裔這個情況,因為我之前讀郭怡慧(Michelle Kuo),一個台灣裔的美國作者的自傳《陪你讀下去》(Reading with Patrick),這本書里講述了她如何教監獄里的囚犯閱讀的故事。我個人不是在美國長大的,所以當我讀到她講自己從小生長在美國密歇根的小鎮上的時候,就好像她打開了一個視窗讓我偷窺進去一樣。她說自己從小長大的小鎮上都是白人,她作為唯一的亞裔從小受到排擠,沒有辦法認同白人文化,但是當時的美國又沒有什麼亞裔作家的經典作品可以讓她認同。所以她吸收的那些“文化養分”都是來自那些當時白人學校裡面不教的、但你可以在邊緣文化裡面找到的那些黑人作家,比如瑪雅·安傑盧(Maya Angelou)等等。她就天天背誦安傑盧的詩,哭著入睡;所以她在長大的過程中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黑人,或者說她一直渴望自己能成為一個黑人。
因為在美國的種族抗爭或各種抗爭的脈絡下,亞裔好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找不到自己的身份。亞裔又不願意從屬在白人的文化底下,然後如果亞裔要施展能動性的話,就要從黑人運動里去汲取資源,這些點都和劉文說的很像。
劉文:的確,因為白人主流文化,無論是異性戀或同志的文化,對於亞裔都是一個非常艱難的處境。如果你是亞裔的男同志的話,你的處境就尤其難,最近蠻多研究都表明瞭約會市場對於亞裔男同志的排擠。有一個很有名現象,像很多同志約會網站的個人簡介會說“不要胖的、不要太陰柔的、也不要亞洲人(no fats, no bottom, no Asian)”,這成為了一種男同志交友的階層。所以如果你要去融入這樣非常種族化的同志社群,你就要犧牲很多,你可能要犧牲自己的獨立性,或者你就要去認同白人的文化。
很多人會問我女同志在這個方面是不是會好一些,那根據我自己的觀察,跟在文獻上看到的來說,我認為整個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對於女同志圈還是有正面影響的。我們比較少看到這種非常公然的種族主義攻擊,當然不是說沒有這樣類似的種族主義互動,但是的確沒有像男同志那樣激烈的種族主義攻擊行為。所以我認為在整個性別種族交織中,女權運動還是帶來了一些幫助。
馬景超:剛才林垚問在這樣的理論中有沒有忽視一個少數族裔的問題,我覺得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引入階級的概念。
然後劉文也講到很多階級的問題,我有兩個很有意思的例子,第一個是說在美國20年代早期,在波士頓有一種生活方式叫波士頓婚姻(Boston marriage)。因為波士頓一直是一個大城市,然後一個受教育的女性是有可能在波士頓完全憑自己的工作活下來的,這一點在其他很多地方是做不到的。所以說兩個受教育的女性可以結成伴侶,共同生活;她們可以自食其力,不去依賴其他的男性對她們經濟上的支持。然後波士頓婚姻非常努力地要和當時在心理學正在形成的女同性戀的概念畫清界限。因為她們覺得女同性戀指的是那種工廠女工,她們就進了一個酒吧,發生一些什麼。她們認為女同性戀指的是那種很變態的事情,而我們是非常高雅的兩位女士,共同生活、追求獨立。
將性取向,然後包括浪漫關系或者性關系的對象的選擇作為一個身份,這件事情本身是很新的。甚至這件事在一開始是非常受階級身份阻礙的,她們不同群體之間是完全沒有團結性(solidarity)的,波士頓婚姻的實踐者覺得自己是受教育的獨立女性,和女同性戀是完全不一樣的。 當然這裡面也有對於病理化和污名化的一個拒斥,但是這種拒斥是建立在“請去病理化和污名化那些窮人”這樣的一個基礎上的,我們也知道在美國階級問題和種族問題又是分不開的。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我前陣子在讀韓裔美國詩人Cathy Park Hong的《小情感》(Minor Feelings),她講到自己曾經在一個酷兒和跨性別的藝術家都很愛去的夜店,她在那邊覺得自己非常受歡迎,她也很喜歡那個夜店。那裡不僅有跳舞、喝酒,還會有詩朗誦和各種藝術活動。它是一個社會邊緣的人聚在一起爆發創造力和互相取暖的地方。然後Cathy Park Hong說她當時非常喜歡這個地方,於是就開始用這個地方辦她朋友的派對,想給夜店帶來一些生意,結果一來二去這個夜店就火了,因為她把派對帶進了藝術圈。但夜店火了以後,那些原本來夜店的窮人、少數族裔就不願意來了。Cathy Park Hong覺得很難過,覺得她把這個夜店給毀了。
這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如果我們無論是去想同志運動、跨性別運動,還是一些美國現在的社會運動和它們的歷史。這些運動一開始都是有許多有色人種參與的,比如說石牆運動,最開始是瑪莎·P·約翰遜(Marsha P. Johnson)扔了第一塊磚,引領了石牆暴動。也就是說拉開石牆運動序幕的,其實是一位黑人跨性別女性;那為什麼石牆運動、同志運動現在變成了海報上有兩個很漂亮的白人男性、他們在一起結婚、然後他們要去迪士尼樂園領養一條狗,這樣一種呈現的模式呢?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很有意思,它不僅涉及到了白人化(white wash)或者中產化(middle class wash)。這里涉及到了酷兒理論的一個歷史背景,酷兒理論之所以能夠作為一個反建制、反規範的理論所浮現,是跟當時艾滋病(HIV)的蔓延,以及大家對於艾滋病完全不瞭解只能任由他蔓延的情況分不開的。因為在那個時候,如果你有同性性行為,那麼你其實無法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死,甚至可能你年紀輕輕就去世了。
這個感覺是非常可怕,你非常努力地去要求政府和醫療公司投入資金,去研究、去阻止這個東西;然後政府和醫療公司就完全不管你的死活,因為很多人覺得你們活該去死,這非常可怕。但是這樣的情況對於當時的酷兒群體起到了一個構建的作用,很多人會說社會主流不管我們,那麼社會主流本身有問題,我們應該從我們的視角出發,去批評社會主流。於是你就處在這樣一個越軌,或者說邊緣化的位置上;然而一旦這個位置變得沒有那麼危險(比如說你這個人比較有錢,你如果有了同性性行為,你也可以花錢掩飾),或者一旦你有一些其他的身份上的特權,能去讓違規變得不那麼地威脅到你的生命,這樣的違規行為就可以變得很酷。違規是可以變得非常的美學化和仕紳化(gentrify)的。違規可以從一個街頭流浪的青少年所做的事情,變成一個非常酷的、平時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中年男性在周末做一下的事情,然後這個事情也完全不會影響到他從周一到周五從事的,非常掙錢的工作。
一旦這個事情變得仕紳化和美學化之後,酷兒理論就會來抵抗它。現在我們也有很多的批評,關於酷兒理論要如何去白人形象、去白人中心化。但實際上這很有意思,因為這個理論一開始是來自於一個非常邊緣、非常底層的位置,然後它慢慢地被仕紳化了以後,我們還要拼命的說,其實你又忽略了底層的聲音,你又忽略了邊緣的聲音。但是我覺得在消費社會內,去除了“危險”成分的“違規”其實是很好賺錢的:“違規”意味著你可以給這些人賣一些不同的商品,同時它是很容易被時尚化的。
郭婷:就Ali Wong說到的,現在有了Urban Outfitters 這些牌子之後,它把事情變得非常復雜,不知道那個滿臉大鬍子、穿得很破的人是一個真正的流浪漢,還是一個嬉皮士(hipster),消費社會剝奪了別人的一些生活狀態。剛才馬景超說到了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任何運動,它的終極目的、終極目標是什麼?或許它曾經的目標是非常明確的,但是它在發展過程中,或者是在所謂主流化、在被看到的過程中,這個運動會慢慢地被容納、被吸收,變成主流的一部分,加固了它曾經所要反對的社會秩序。所謂的在對身份的爭取過程中,被看到的身份還是因為它擁有那些社會資源,擁有的那些文化標記,使得它容易被看到。
我在香港認識有些老年的女性長輩,她們從小到大其實都知道自己是女同志。她們不需要出櫃,因為她們其實來自中產家庭,有著中產身份。她們可以和自己的女性朋友住在一起,周末她們也和家人一起飲茶,大家也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但大家都不說穿。她們也是非常優雅地兩個人一起生活,她說這是我最好的朋友,大家就覺得不用所有人都覺得好,但是我們不說穿她的事情就可以了。
最近香港也有一部根據相關研究改編的電影《叔叔》,講述香港曾經的底層同志圈的生活。其實大部分人是沒有辦法去做出一些爭取身份的行為的,所以他們選擇了主流化,因為這是他們唯一能夠找到的,被接受的一種方式。電影的最後兩個人也是分別回歸各自的家庭,因為他們覺得我的主流生活是我花了一輩子努力工作得來的,現在我在香港有一層樓、有房子、有家人。這些主流生活是我來香港目的,我這一輩子就是為了這些東西。所以我不能輕易地因為一個不被社會認可的身份,去放棄我已經被社會接受的身份。
我們剛剛說到很多東西方或者二元對立的理論,可能是來自於西方社會的哲學家或者學者。那如果亞裔學者想要有一些的突破,可能他們需要做一些社會田野,反映不同的社會現實,用不同社會現實來挑戰既有理論。有的時候是從自己的文化或者哲學裡面,找出一些東西來挑戰一個理論。那我現在在思考,從文化霸權的建立或者文化差異的形成這些方面來看,是否存在其他對話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大家在這方面有沒有什麼想法。
劉文:我覺得這是當下的一個很困難,但也很重要的問題。其實酷兒理論它一開始是強調性欲或同性戀(homosexuality)的,它本身是一個西方特有的科學史。 同時這個理論也必須要找到它的他者(other)。在福柯的《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裡面,他認為西方性對立就是中國的性,中國的體制跟西方的精神科醫學經歷了完全不同的發展。因此很多進一步的分析都會認為,亞洲整體的性有一個性的階層或者系統。比如說在90年代的時候,香港學者周華山就會強調“同志”這個概念,是跟中國以及華人文化緊密聯合的。當然這個論點有很大問題,但我想先說說他的論點,他認為同志這個東西是完全融入於華人文化、華人社會的,所以你身為一個同志,你不用出國也沒有關系,家人都是默默地接受你,他說這是華人文化裡面的一種“溫良恭儉讓”的潛在包容性。所以這種認識所造成的問題是,當中國的性成為西方的對立面時,所有分類(bracket)下的問題和認識也遭受了另一種本質化。
像在台灣而言,我們會認為說中國的性系統或許不能夠代表全亞洲的性。但對於西方人來講,亞洲的性就是西方的對立,所以現在我們會講亞洲酷兒研究(queer Asian studies)。有人會說我們不再講跨國研究(transnational study),我們應該要講區域性研究(regional study),應該要去關註每一個地區裡面的特殊性。
但是,關於怎樣去理解整個亞洲酷兒與西方對立所造成的一些問題,我也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不過我認為這樣的中西方對立之下會產生第二種問題,比如說台灣這20年的酷兒運動是比較旺盛的。台灣在2019年建立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有一些台灣籍或者是美國籍的所謂的酷兒學者就會批判說台灣的運動就是一種自由主義酷兒運動(queer liberalism),是酷兒運動的西方化跟主流化。
但其實這樣的框架又再次套用了西方的論述。來到一個非西方國家,同志必須爭取權利的一個脈絡,所以你將這些運動批判為完全沒有任何根本性、激進性,說它是一個完全主流化的表現,我認為是太簡化這些運動的動能了。尤其現在有一個新的說法叫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它指出即使在華語語系裡,我們也不要把中國當成一個絕對的代表,而是去探討這些華語文化中的特殊性。其實中、港、台的同志文化里有非常多的連接,但如果很多學者用酷兒理論把台灣打成是“奔向西方主流化”、“喜愛帝國主義”的這種同志運動,中國本土的運動才是唯一社會主義酷兒的未來,那麼又會產生另外一種地區上的,或者在華語社會(Sinophone society)里的對立。
所以這個問題真的非常復的,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一個很大的功課。尤其是現在所謂的新冷戰爆發,中美的這種對立其實對酷兒理論也有非常大的影響。
郭婷:對,我剛才也想到華語語系研究,最近有一本新書:《跨太平洋華語語系的跨托邦》(Transtopia in the Sinophone Pacific)。雖然我還沒有看那本書,但它用了“跨太平洋華語語系”這樣的一個概念,也包括了北美亞裔群體。
那我想問一下馬景超,你從哲學領域出發,在哲學研究裡面有沒有一些這方面研究的心路歷程呢?
馬景超:剛才劉文指出了本質化的危險和對於中國是一種社會主義酷兒烏托邦的一種想象,以及如何去討論這種東西方之間的區別,怎樣既要討論它們的不同,又不要把它們本質化。然後,其實我自己最感興趣的不是這個區別,而是東西方互相之間的關系。
一個是劉文所講的,如何去以亞洲作為他者(Other)。我自己講課的時候,我的學生總會說我們美國女性的處境已經很好了,我們跟伊朗、跟印度、跟中國比一下,她們就總會挑一個亞洲國家,而不是南美洲、非洲,其他這些南方國家去比較。歐美社會對於性別的想象非常依賴亞洲這樣一個他者。我所處的社群,一個在使用中文、同時又在美國學習的這樣的一個學者小群體裡面,我們也經常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在簡單地搬運歐美的知識,我們為什麼要搬運這樣的知識,我們還要不要搬運這樣的知識?
這里有個知識生產的問題,我們會覺得歐美的女權主義發展很早,所以我們可以學習先進經驗。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家都會面臨的問題,就是你在讀書的時候,一方面你會覺得這本書寫得真的太有意思了,然後你馬上就會想著說這本書和我在國內的處境有沒有關系?這本書和我看到的國內的事情有沒有關系?如果有關系的話,它是一個怎樣的關系?哪怕像我現在沒有在專門的寫這方面的問題,但是大家讀書的時候,有時候還會難免想到這個問題。
我自己的話,我是很想小心地做這件事情。每次我做一點搬運,我都會說雖然我搬運了,但是請大家不要用,把自己置於這樣一個非常尷尬的處境。我一直很想強調我是搬運了,但是大家千萬不要生搬硬套地來用,大家千萬不要讀了以後就不加思索地去引用它。大家一定要想一想,在我們的生活中是否有這個議題,是否有這個概念,或者是否有這樣的一個社群。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廣義的翻譯的政治,不僅是你把英文的東西翻譯成中文,而是你自己的學習和工作也是一個翻譯的過程。包括你用中文輸出思考,也存在著一個翻譯的過程;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或者我自己的位置是什麼,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需要去關心的一個問題。尤其是如果我的思考會被關心性別議題的朋友們看到,那麼我要如何避免成為一個簡單的搬運工的角色。
我覺得哲學作為一個學科,常常把自己的門檻拉得過高。這個門檻有兩個意思,一個是說它是否拒絕去聽一些人的聲音,如果你是女性、是跨性別,或者是酷兒,那麼我們就不太需要把你當真。一些人因此被拒絕。另一個是一些討論因此被拒絕。就是如果你討論的是性別問題,這就是一個非常小眾、非常邊緣的,一個不是“真正哲學”的議題。我們在這里討論實體的本質,你卻在討論性別,那請你到小房間里自己討論去吧。這個是在哲學界里,大家需要去跨過的一些門檻。但另一方面,如果你不暫時跨這個門檻,大家一些人坐在門檻外互相取暖,其實也是很開心的。
林垚:在你們系裡這個情況是不是相對要好一點?因為你們系走的路線跟北美大多數學校的哲學系是不太一樣的。
關於馬景超提出的問題,我記得Kristie Dotson就寫過一篇論文,叫《How is this Paper Philosophy?(這篇論文憑什麼算是哲學論文?)》說的是她以前研究黑人女權思想的時候,總是被其他哲學家問:“你給我講一講,憑什麼你這篇論文是哲學論文?”搞得她非常的火大。但是好像這幾年,哲學界的很多人開始反思這個問題。我比較好奇是不是歐陸哲學或者現象學的領域,這情況要比那些比較主流的哲學系要好一點?
馬景超:我覺得這個哲學系不僅是要做歐陸哲學,可能它還需要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偏向才會有幫助,因為如果歐陸哲學完全做歷史的話,大家也可以研究亞里士多德嘛。
我覺得歐陸哲學有一些政治和批判理論的偏向,但是另一方面,分析哲學領域里也是有很多人在做性別問題的研究。我這兩天剛好在旁聽一個跨性別哲學(trans philosophy)的會議,最近很熱門的學者Robin Dembroff,他就是學分析哲學的。
也是跨性別哲學的一位新星吧。包括Talia Mae Bettcher(在過去作為跨性別者出櫃),美國跨性別哲學界的非常資深的一個前輩,TA也是做分析哲學的。所以我覺得做這方面研究一個是要看你有沒有一個批判理論的面向,另外一個就是看你有沒有一個政治和社會正義的面向。如果你有這兩個面向的話,那我覺得你的研究和你的具體方法或者你的思想資源也沒有那麼相關。
林垚:既然你說到Robin Dembroff、Talia Mae Bettcher還有社會正義政治,我就想聊一下聽眾朋友們可能最近有所聽聞的相關爭議。
最近這幾年,跨性別權益的爭論首先在公共政治界開始爆發,後來被引入到哲學界內。大概2013年左右,美國開始有關於跨性別人群到底要用什麼樣的廁所的爭論:男跨女到底能不能用女廁所、女跨男到底要不要用男廁所等等,然後就引起了保守派很大的反彈。女權理論內部也出現了很嚴重的站隊以及相互攻擊現象。
有一派是自稱跨性別包容女權(trans-inclusive feminists),然後把另一派稱為跨性別排斥女權(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s, TERF)。然後被稱作TERF的團體特別討厭這個詞,她們自稱為性別批判型女權(gender critical feminists),給出的說法是:女權理論本來就是要批判社會性別的,因為是性別是構建的,而現在跨性別人士常常是要把自己包裝打扮的更加符合主流的審美和刻板印象,包括連上廁所都想要上按照主流的劃分的那種男女廁所,所以在這些自稱“性別批判型”的女權主義者眼裡,就是對女權主義的背叛和倒退。但是反過來,對“跨性別包容型”的女權主義者眼中,恰恰是TERF們是在打著旗號進行恐跨,是在排斥跨性別的人群享有他們應有的權利。
近來因為哈利波特的作者J.K 羅琳開始加入論戰,這個事情就出圈了,普通大眾也開始爭論這個事情。酷兒理論界也參進去了論戰,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接受了採訪,批評了羅琳。
這里我想替聽眾們請兩位嘉賓來評價一下這場爭論,同時再提兩個相關問題:一個就是說酷兒理論和跨性別研究到底什麼關系? 為什麼這幾年大家忽然開始談論跨性別研究了,它是通過酷兒理論衍生而來的嗎?還是說這兩個理論本身是並行的?
另一個是就像幾位剛才都提到的,酷兒這個概念它本身是一種關系性的概念,是這個群體和主流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反叛的、挑戰常規的關系。那麼這是不是意味著它對“跨性別”這個概念本身有一種潛在的挑戰性?因為如果按照“性別批判型”女權人士的說法,“跨性別”概念所做的只是從主流社會認可的一種性別跨到另外一種被認可的性別,最後還是在框架裡面打轉。這裡面是否存在著一些沖突?酷兒理論對這種看法應當如何回應?
劉文: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從運動脈絡開始梳理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在整個同志運動的主流化階段,特別是從1990~2000年初這個階段,我們會看到曾經在1960年代比較融合的酷兒的訴求跟性別的訴求,分歧越來越大。
很多的酷兒學者認為,這是因為在主流化的階段,“性欲”成為了一個私有化的物品。很多主流訴求利用了“隱私(privacy)”這個概念,比如在我家,我想要跟誰上床,這個不是政府可以管的事情。所以當時的同志運動走的是這種性私有化(privatization)路線。但是性私有化也造成另外一個問題,那些比較有公共表徵的性別表現(gender expression)是看起來“不正常的”,這些人就被歸類為“不適合納入同性戀(gay and lesbian)主流社會”的群體里。因此我們在90年代後看到了運動的分歧,跨性別者或者性別多元者認為他們需要有自己的運動。因為當主流的同性戀的私有性行為被保護了以後,他們的公共的性別表徵卻變成了一個受到公眾攻擊的對象,所以這個問題讓運動開始發生造成分歧。也是在這個時期,有一群學者認為我們必須要更清晰地去思考,跨性別可以帶回給酷兒理論的動力。
另外一個脈絡是女權運動的脈絡,現在有比較排斥跨性別的女權主義。在某一種程度來說,它是女權運動裡面的一個分歧。其實女權運動里一直都有這種本質派的,比如說認為那種母親孕育了上帝(mother of god);女性比男性強,因為女人有子宮有乳房,更貼近地球、有超能力的這種文化女權主義(cultural feminism)。在70年代,它是發展特別旺盛的一個派系。在70年代,還有女同性戀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這個派系認為,女同志如果要抵制父權的霸權,她們必須要完全離開父權社會,甚至要離開她們對於異性的欲望。所以女同性戀這個身份不僅僅是你的欲望,也是一個政治的身份。那時候她們就會開始排擠有跨性別欲望或身份的,無論是男性化的女性(butch)或者是男跨女的對象。這樣的一種路線當然是被後來的運動所批判,但該路線還是一直蔓延到現在。又因為整個美國的主流政治,特別是保守派都在利用跨性的權益作為一個他們訴求認同的項目。包括墮胎權或者是跨性可以使用的衛生間等等,都成為保守派製造恐慌的議題。
最近在加州有一個事件特別影響華人的社群。我自己有一些華人媽媽朋友,她們會接到一些中文訊息,說加州要通過一個法令,要更改性教育課程。現在只要這個民主黨提出的法案通過,幼兒園的小朋友就要開始去認識什麼叫多元性別。那中文信息就會把這解釋成一種很可怕的東西,就是你小朋友如果想要跨性的話,你幼稚園的老師就會鼓勵小朋友去跨性。這些家長聽完都瘋了,他們覺得我送我的小孩去公立學校,然後老師居然要教ta要怎樣去變成跨性,他們就會想到這種很性恐慌的事情。其實對大家來講,認識性別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尤其如果你是一個跨性的小孩,你可以有一個很支持你的環境,你的同學也都可以理解你,那麼憂鬱、霸凌、自殺等現象可以大幅減少。
很可惜的是,我認為美國現在的社會太分裂了,他們就會拿這樣的性恐慌去製造政治對立。所以這種東西其實它已經打包了(package)以前女權運動跟酷兒運動期間沒有解決的這種路線分歧,變成了一個包裝著保守訴求的性恐慌,同時為保守派爭取選票。特別是這些華人家庭,他們可能也想要全民健保、想要比較好的移民福利,可是他們看到民主黨在搞這些多元性別跨性政策,他們可能就會去認同川普。這也是我看到的一個還蠻令人憂心的現象。
馬景超:剛才林垚提到,廁所爭論大概是從2013年開始的,然後2015最高法通過了同性婚姻。那麼像劉文剛才所講的,保守派在挑選議題的時候,因為同性婚姻已經大勢已去了,所以我們要推出一個新的、看起來非常可怕的議題。所以我覺得並不是說這個議題、或者說這樣的爭論之前不存在。女權主義的分離主義和女性空間要排除跨性別者的爭議,從80年代的密歇根音樂節開始就一直存在並延續著。另一方面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從美國社會和政治去看,保守派在怎樣一個時間點,把怎樣的一件事情推到了風口浪尖。
說回我剛才提到的一個話題,現在這些議題都是很輸出的,美國保守派所制定的議題會變成一個全球議題。相較於種族議題,性別議題和性別身份的焦慮是非常容易輸出的。我們很快就會去抓住這樣的一個性別身份的焦慮,但是我們甚至都不瞭解我們身邊的跨性別者他們需要什麼、他們的議題是什麼,我們身邊的一些跨性別的政策是什麼,就感到了焦慮。
還有就是林垚剛才所指出的,酷兒理論和跨性別理論的關系。我覺得跨性別理論本身也是千差萬別的,它的取向非常多元。大部分我所接觸到的理論學者,他們還是非常認可酷兒理論和女權主義理論的很多思想資源,包括女權主義理論對於社會性別規範的批判和對於身體本質論的批判,也包括酷兒理論對於社會規範的一個思考。
當然在具體的論證上,大家會有各種不一樣。比如說到性別規範,大家如果只通過流行文化來瞭解跨性別者,會覺得跨性別者非常遵守性別規範,比如金星就一直穿得非常美,打扮得非常符合傳統上的女性形象。但實際上,一方面很多跨性別者對於性別規範的遵守是一種生存的策略,我們也可以想象到就如果跨性別者不遵守性別規範的話,ta所要付出的代價是極其大的。出於生存策略,ta就不得不去遵守一些規範。
另外一方面,在跨性別社群內部,包括理論社群內部,對這個現象也有很多的討論,並不只有我們在流行文化中看到的跨性別形象。包括大家現在可能看到美國的性別非二元者(gender nonbinary),現在出櫃的性別非二元者越來越多了。同時,如果我們去關註一些學術文章之外的理論,比如說大家在網上進行的討論,它實際上是非常有創造力的。比如說網上前兩年tumblr上有一個很大的討論,就是說跨性別一定要有性別焦慮(gender dysphoria)才叫跨性別嗎?性別焦慮指的是你對於自己性別身份的不認同感,以及它帶來的一種痛苦和不安。有的人就說我對自己的身體並沒有不安,但是我對於社會的性別規範完全的不認同,我堅決不想進入社會的二元性別,我這樣算跨性別嗎?像這樣討論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創造性。
某種程度上來講,我覺得跨性別者接過了酷兒理論的大旗,就是為我們所有順性別者去開闢一些非常新鮮的領域,然後在一些我們想象不到的地方去撬動社會性別規範。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轉向了跨性別理論的研究,我覺得實際上現在的運動還是承繼了很多女權主義和酷兒理論的關切,但是因為這個運動現在面對的是一個不同的社會、不同的焦慮,因此它要去開發出來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郭婷:我想最後討論兩個問題,一個是剛才兩位都提到一個情感的力量。不管是保守派為自己的政治籌碼製造情感恐慌、情感焦慮,或者是剛才提到的情感理論其實有一個社會修復的作用。能不能請大家再討論一下,除了恐慌、羞恥這些情感之外,有沒有情感理論在社會上起到修復作用的例子?
另外,我們也有一個吐槽環節。因為我知道劉文在美國有一個終生教職軌(tenure track)的職位,然後又放棄了職位回到台灣,那是什麼促成你這樣的決定?那回到台灣、回到亞洲社會、回到中文世界之後,有沒有其他的一些可能需要重新適應的地方?
劉文:我最近也在關心社會修復的議題,其實像現在全球大瘟疫的情況下,酷兒社群有一個強大的修復網路。尤其是結合無政府(anarchists)傳統的一個社會網路,像他們會在Instagram、telegram建立一個互助小組(mutual aid)。比如他們會知道身邊哪一些社群的朋友,他們可能因為殘障、或是因為比較容易感染病毒不能夠出去買菜等等。於是他們就建立這種自發性的網路,幫助大家去採購食材;此外,他們還有很多這種關懷性的(caring)線上聚會等等。
可能這東西它沒有那麼政治化,但它其實是整個酷兒運動可以一直維持下去的原因。因為你讓一些都是被社會邊緣化、排擠的人,去擁有一種可以建立自己社群的力量。尤其是他們重新定義了什麼是關懷,一種離開血緣家庭後的關懷關系(caring relationship),我認為這是整個酷兒社群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修復動能。
另外,我最近還在做的是迷因(memes)的一個修復動能。比如我很關註的香港的運動,還有近期的奶茶聯盟(milk tea alliance),它其實也是從香港運動發起,然後去聯合台灣,現在在泰國發展的一個學生運動,他們會依靠很多的迷因去發展這種跨國連接。
即使可能他們的很多政治訴求錶面上沒有那麼一致或者接近,但他們有地緣政治上的批評。我為什麼認為網路的迷因文化很酷兒,因為第一,所謂的奶茶聯盟它是脫離這種血緣的,或者國家主義的關系的;它想要去超過國際邊界去找到這種連接。所以我其實對這個現象比較有興趣,我認為它是可以持續發展下去的。
然後其實為什麼會想從美國離開的一個原因,其實我自己也是感慨很深。因為我一直都有參與不同的社會運動,以種族為主的運動後,我其實對於美國的自由派是有很大失望的。首先,我認為亞裔要在美國社會要找到自己的政治主體性,你需要花很大的工夫,特別是如果你要融入主流的亞裔美國人的運動,你必須要有強大的美國認同。但這也是亞裔運動的一個問題,就是它其實還是要以美國人的身份去改變美國的體制,但我個人比較有興趣的還是跨國的連接。所以,當時我所參與的運動,也都是跟韓裔、日裔、中國裔的朋友,去做一些比較跨國的運動。久而久之,我就發現這些運動在美國本土的自由派裡面是非常次要的。對他們來講,國內的議題才是最重要的,這個也反映到了學界他們所關切的問題。像我當時所在的系其實是女性,性別和性研究(Women’s,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它其實應該是一個非常前沿、進步的系,我也認為我的同事非常的進步。但當疫情來臨的時候,你會發現美國還是那種主流的美國人,一開始他們並不認為這個疫情會有多麼的嚴重。他們也不能理解這種中美角力之間被犧牲的很多其他的主題,比如說他們會認為你不能夠批判中國,因為批判中國就等於種族主義。這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問題。特別是在性別學界,在美國你要有超越主流自由派的話語權,是一個蠻辛苦的過程,要找到戰友也是比較困難的。
第二個是在美國學界,即使是在一個非常進步的院系,像我們學校,他們會認為有色人種其實就是拉丁裔和非裔。亞裔對他們來講,就是國際學生或者國際學者。他們不認為亞洲人也經歷過種族壓迫,他們認為如果你是一個亞裔,你的壓力就來自於你的語言不好、不能適應文化。這也是我離開的原因,我知道在美國學界,就算是你身處在非常自由派的環境之下,你要作為一個亞裔去發聲也很困難。你的研究還是必須跟美國主流對話,也就會產生相應的問題。
另外也是因為目前在亞洲的社會運動其實更加有生命力(vibrant)吧,特別是台灣在2014太陽花運動之後,整個社會的改革跟氣氛是很適合發展的。加上最近性別議題在台灣也變得非常重要,所以我認為現在是回來的好時機,我也可以去參與這樣的社會議題。我身為一個台灣人,其實已經離開台灣快20年了;如果我現在不回來的話,我很怕我會變成老華僑。如果我要更加進入社會脈絡,同時對我來講比較好使力的地方,可能還是台灣的這個環境。
郭婷:感謝分享,剛才也說到一些很重要的議題,我就想到我們時差第一期、第二期其實也談到,就是美國內部種族話語有一個泛亞裔的這樣一個概念,後來也變成美國主流自由派話語的一個脈絡,很難突破這個界限。我記得有一些美國亞裔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ies)早期關註的是美國內部的多元化,但那個多元化也是非常固有的多元化的定義,建立在國族之間的認識上,有時候是和世界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相互矛盾、背道而馳的。在60年代美國第三世界解放陣線(Third World Liberation Front)建立的時候,他們其實擁抱的是毛主義,非常支持文化大革命,這是我覺得非常諷刺的一點。
馬景超:劉文之前有提到亞裔的一個文化環,他把你視為一種文化。我自己這方面讀的很少,所以我提不出來什麼特別好的批評,但大家知道文化人類學現在對於文化這個概念是非常批判的。亞裔無論乾嘛,大家都說那是你的文化,這非常的奇怪,就無論你愛吃什麼都是你的文化,無論你聽什麼音樂都是你的文化。
我遇到過的最奇怪的是曾經有一個白人說ta從小在家裡面都過中國新年,但是ta現在長大了,覺得這樣子非常的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今年ta想自己再辦一次中國新年派對,ta就問我“你能不能來參加派對,這樣我就不是文化挪用了”。這話讓我哭笑不得。
可能ta認為你這樣的一個身體,擁有這樣的文化就非常正宗,就好像你做出來的左宗雞就會比他做的左宗雞好吃一樣。文化只要是安在你身體里就更加正宗,就更值得消費,這就非常奇怪。這可能是我對於美國社會對於多元文化主義的一個比較廣義的吐槽。
郭婷:最後按照我們的新傳統,想請大家在結束的時候說幾句比較有希望的話。
馬景超:說到比較希望的話,對我來說最有希望的事情就是大家坐在門檻外面,抱團取暖聊天吃零食。我自己也越來越覺得劉文講到的互助網路可以非常得廣義,不僅是說在在現在這樣一個封鎖(lock down)的情況下,你去幫助你的鄰居或者是一些本來身體就不是很好的朋友,而是說我覺得大家平時抱團取暖就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事。活著不容易,抱團活下去。
然後之前在Facebook上經常看到台灣朋友討論同溫層的問題,大家都說我們怎麼樣打破同溫層,我一直在同溫層裡面非常的舒適等等。我覺得那不是挺好的嗎,那就繼續舒適下去。因為我覺得很多人如果是女性,或者是酷兒,或者是跨性別,你的日常生活可能是不太舒適的,如果你能找到一個舒適的同溫層,那麼這就是一個你們休息的地方。我覺得你應該有一個能夠休息,能夠不用解釋自己,能夠不用擔心大家對你抱有敵意的地方。
如果你能找到這個地方,或者你能成為別人的舒適圈,我覺得這是我能想到的最有希望的事情。
劉文:學術界很多的工作是很孤立的(isolating),就是一個人做的事情,而且我認為學界特別會促進超高效生產(ultra-productionist)這種心態,就是所有的東西都要拿積分、都要發表、都要取得最大的曝光,所以我也很同意所馬景超講的這種「活著不容易,抱團活下去」的精神。
如果我們可以做一些回到學術,或者說集體創作的本質,我覺得就是像大家這樣的討論,以及理論與社會的結合,還有知識的運用。如果我們看一下整個性別運動的歷史,在這30年間,它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尤其是在北美社會,你可以看到我的學生沒有一個人會不知道什麼是跨性別;甚至他們知道講錯的話,可能會是政治不正確的( politically incorrect)。從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這個運動在二三十年間對於社會產生了多麼巨大的改變,所以改變是很有可能的。有些事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會忘記,像階級或種族的運動會讓我們覺得有一種很難完全翻身的感覺,但只要這些運動之間能夠有更多的對話,那麼改變就是有可能的。你可以想象90年代朱迪斯·巴特勒出了一本跟性別展演(gender performativity)有關的書,現在有多少人必須要理解什麼叫性別的展演。其實這個運動是真的可以影響很多人,回到性別、性別理論還有酷兒的運動,我認為我們是要對這個社會有所希望的,這些運動其實是可以影響社會的。
郭婷:那最後我也想提一個網飛的劇叫《性愛自修室》(Sex Education),我非常喜歡這個劇,它裡面說到英國的種族跟性別上的一些現狀。最後我也在思考,我們怎麼更打破一些邊界,通過把團做大,讓更多的人可以一起取暖,讓更多的人可以有些地方休息。
參考書目:
Robin Dembroff, “Beyond Binary: Genderqueer as Critical Gender Kind,” Philosophers’ Imprint 20 (9):1-23 (2020).
Talia Mae Bettcher, Transgender Studies and Feminism: Theory, Politics, and Gender Realities, Hypatia: 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 24:3 (2009). Special issue co-edited with Ann Garry.
Howard Chiang, Transtopia in the Sinophone Pacific . Columbia UP, 2021.
Michelle Kuo, Reading With Patrick: A Teacher, a Student and the Life-Changing Power of Books.
劉文,Assembling Asian America: Psychological Technologies and Queer Subjectivities. (winner of the 2018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s First Book Prize, and currently under contrac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__________. and Macleod, C. I., Bhatia, S., “Feminisms and decolonizing psychology: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Editorial introduction. Feminism & Psychology, 30:3 (2020) 287-305.
__________. 〈酷兒左翼「超英趕美」?「同性戀正典化」的偏執及臺灣同志運動的修復詮釋〉,《應用倫理評論》第58期,2015, 頁101-28。
馬景超,“Young Activists, New Movements: Contemporary Chinese Queer Feminism and Transnational Genealogies” (Co-written with Liu, Wen and Ana Huang) Feminism & Psychology 2015, Vol.25 (I) 11-17.
__________. (翻譯)導讀巴特勒,薩拉.薩里(Sara Salih)著 ,重慶大學出版社,2018.
__________. (翻譯)導讀波伏瓦,厄蘇拉·提德( UrsulaTidd)著,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
__________. 長久被視作政治冷感的華裔,怎樣在美國社會集體發聲?
__________. 兩代美國左派社運詞匯的變遷
__________. 美國的女權、女同性戀與酷兒
Judith Halberstam, “Transgender Butch: Butch/FTM Border Wars and the Masculine Continuum,” GLQ (1998) 4 (2): 287–310.
David Valetine, Imagining Transgender An Ethnography of a Category. Duke UP, 2007.
Eve Sedgwick,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Duke UP, 2003.
Chong‐suk Han, “No fats, femmes, or Asians: the utility of critical race theory in examining the role of gay stock stories in the marginalization of gay Asian men,” Contemporary Justice Review Issues in Criminal, Social,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Volume 11, 2008 – Issue 1, 11-22.
Trans Philosophy Project, https://transphilproject.wordpress.com/
影視劇:
Pose (電視劇,2018年首播) 1980-90年代,紐約非裔/拉丁裔的酷兒社群的生存處境,及其首創的「舞廳文化」(ball culture)與”Vogue”式舞蹈等
Sex Education:英國青少年的性與愛,在此之外細述英國較少討論的種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