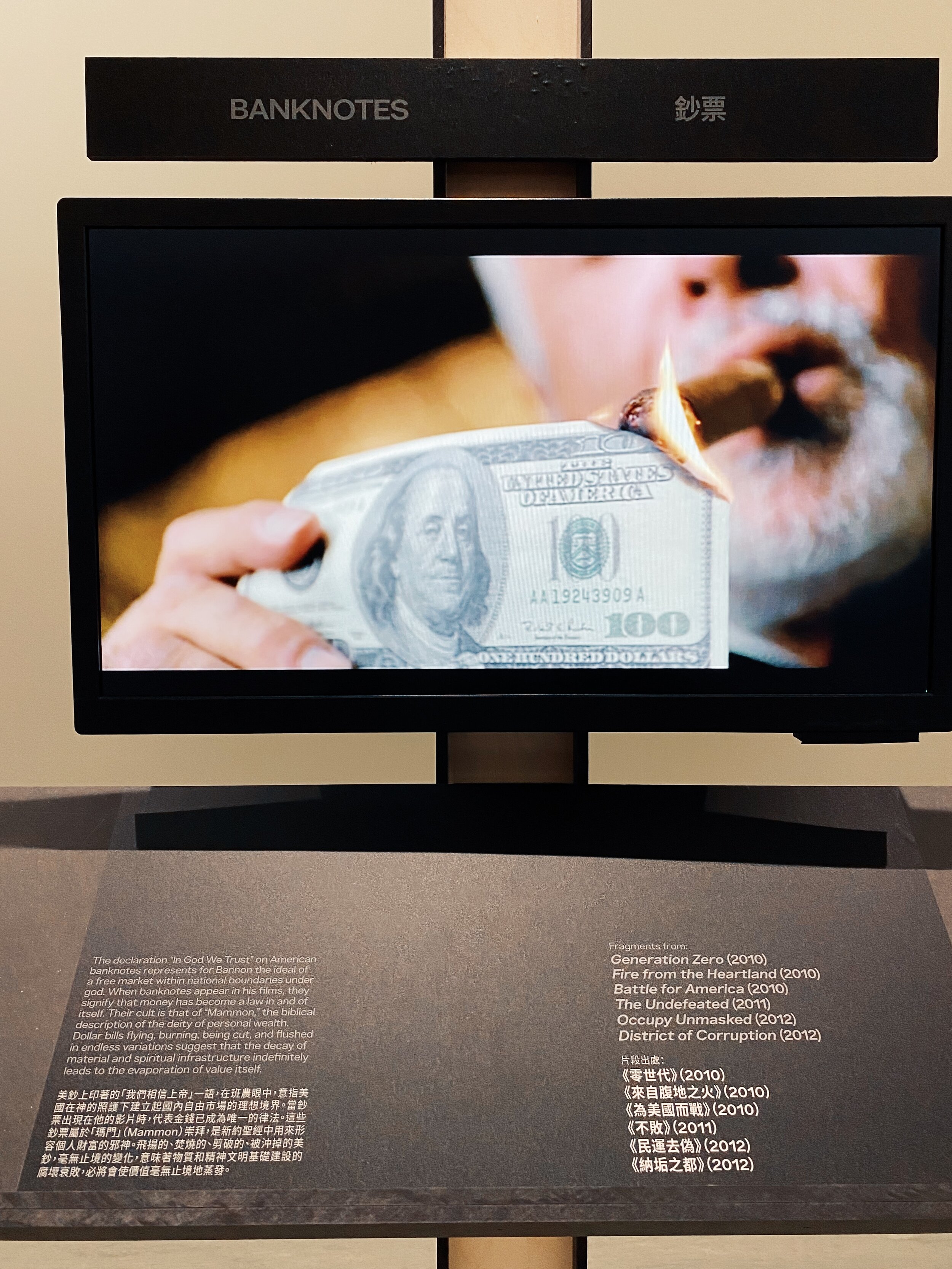《尋愛小說家:海史密斯》Loving Highsmith
成功的小說家總是多情的。派翠西亞.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在她的日記中寫道:「當你心中浮現一個念頭卻不去執行,它即會在體內腐爛。」
1921年生於美國德州的海史密斯,這輩子共累積了22部小說。她敘事手法的細膩與驚奇,讓她受到多位名導演的親睞,著名小說包含《火車怪客》、《天才雷普利》,以及女同志經典《鹽的代價》都被翻拍為電影。在1995年逝世後,透過海史密斯的日記與和她家人及愛人的訪談,促成了這部紀錄片《尋愛小說家:海史密斯》—— 寫過無數迷人並高度複雜角色的海史密斯,終於也成為自己電影中的主角。
海史密斯在日記中將自己比喻為「永遠的尋愛者」(I'm the forever-seeking)。即使50年代的美國已有相當旺盛的同志文化,基於政治的因素,同志在公開場合仍被視為道德上的禁忌。不滿於美國的保守和狹隘,她在歐洲大量旅行,加上她對法語、西班牙語,甚至德語的熟練,使她的愛人們遍及巴黎、柏林與倫敦。
紀錄片的訪談中,這些愛人們對於海史密斯的記憶都是相對片斷的,彷彿也透露了她與這些女人們的關係,靠著大量書信與想像在維繫。而海史密斯的本質是一名孤僻、偏執、悲觀、多情,又可尋歡作樂的工作狂:她在人生與愛情的後期,拒絕再與別的女人同居,為了自己與自己的書寫而活。
即便如此,《尋愛小說家》透過與這些前愛人的對談,讓我看到不少海史密斯的迷人細節。
一名同為作家的愛人瑪莉珍.米克(Marijane Meaker)說,初次見到海史密斯時,她覺得驚奇,因為印象中作家總是比較邋遢的,可能只關心自己的小說與貓,但海史密斯卻是相對穿著華麗的,具有獨特個人魅力。海史密斯在歐洲的酒吧與搖滾音樂家大衛.鮑伊(David Bowie)喝酒,並大方地請在場的每人一杯shot,就因為她當天身著三件式西裝。
米克描述海史密斯嗜酒如命,每日早晨都會邊工作邊喝光琴酒混合柳橙汁的飲料,與她預設海史密斯是自律、清醒以至於創作量驚人的狀態有高度反差。米克在紀錄片中說:「沒想到這麼會寫的人,居然會讓自己處境這麼脆弱。」或許米克所說的「脆弱」,即是指涉海史密斯在任何關係中,都無法全然透露自己的黑暗面,這或許也是她一段關係換過一段的原因之一。酗酒成為她逃避情感的模式。
雖然「被她征服的人數多到可以辦女人節」,但海史密斯也曾因為愛上有夫之婦,毅然決然在英國郊區買下整棟房子,就為了能與對方共進早餐。對於理想的愛情生活,她透露過,希望和伴侶同居於無人打擾的鄉村一起生活的渴望:「柴火與樹枝,蘋果和無花果,沒有電話和訪客,只有我們工作、滾床,還有今天誰煮飯的小世界。」海史密斯也為其他愛人寫道:「喜歡妳為我生命帶來的輕盈,輕盈指的是沒有沉重。」顯露她曾盼望藉由愛情得到心靈傷痛的救贖,與不同對象擁有多樣的情感交流。
我們難以評斷海史密斯是否是情場上的玩家,但她這輩子深愛的,卻也得不到的,可能是她母親的愛。紀錄片提及被外婆帶大的海史密斯,長大後發現自己的母親曾經在懷她時想過要墮胎,也因為懷她時與另一名非她生父的男人再婚,日後與海史密斯保持著相對疏離的關係。
這個經典的伊底帕斯情結,當然並非是海史密斯身分建構的成因,卻也使得她在開始尋覓親密關係時,經歷許多痛苦與創傷。包括,在知道母親不接受她的性向時,她也嘗試與男人交往和性交,甚至進行過性傾向矯正治療。
經歷過被拋棄與被拒絕的痛苦,海史密斯下定決心「要把生命中每一個災難變成美好的事物」。成為小說家的過程,即是她用書寫的方式,替代自己無法經歷或擁有的人生。一個人的生命太過微小與局限,創作即是採取自己的生命經驗,並用想像力將它擴充成為文學的形式。
海史密斯曾說:「寫作是唯一能感覺體面的方式。」她對情人的愛難以持久,但對寫作卻十足地忠貞。她能忍受獨居的寂寞,為了達到「全然的安靜」,透過文字將自己的遺憾轉換為一篇又一篇炙熱且細膩的故事。
在解除一段短暫的婚約後,為了支付自己的心理諮商費,在聖誕節的購物旺季,海史密斯到紐約市的Bloomingdale's百貨公司打工。這短暫的工作經驗,讓她寫出了同志文學的經典著作《鹽的代價》,後來翻拍成電影《因為愛妳》,勾勒一名在百貨公司工作的年輕女子愛上有夫之婦的故事。
與其說《鹽的代價》是第一部有「圓滿結局」的同志小說,它更是關於年輕女性對於自我的性向探索。書中的年輕女子泰瑞莎,從仰望謎樣的有夫之婦卡蘿,直到全然地愛上她,卻遇到無法迴避的社會因素而分開,經歷過自我成長的過程又再度相遇的故事。在紀錄片中,記者問海史密斯,她是否是有意識地安排這個正向的結局?她說,是的,無論她們最終會不會在一起,至少她們有嘗試想要一起有個未來。
這個嘗試,與能夠想像未來「可能性」的勇氣,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何其重要。海史密斯曾說:「能相遇的都是活下來的人。」海史密斯的大膽,除了她對自己人生的開放想像與不害怕嘗試愛情,也包含她能敏感察覺「罪惡感」的存在如何影響個體的決定。
正由於海史密斯的書寫關注人的執念與原生慾望,因此創作題材經常環繞於性愛、犯罪與死亡的情節。她富饒興味地表示:「正因無法完全了解謀殺,所以才感興趣。」
某種程度上,她筆下的角色都是能夠遊走在道德邊際的人。最明顯的即是擁有多重身分的連續殺人犯雷普利,他能夠執行自己的慾望而毫無牽絆,不需抱持著歉意活下去。而《鹽的代價》中的卡蘿,則是違背異性戀常規化的束縛,以及親權的勒索,選擇追尋自己所愛。這兩個事件當然無法直接類比,但我們彷彿可以體會到海史密斯性格以及書寫的核心:她寧願透露出兇殘的仇恨與越軌的慾望,也不願受制於世俗道德的枷鎖而過著平凡無奇的一生。
海史密斯在她1947年的日記中寫道:「讓所有惡魔、慾望的魔力、激情的熾烈、貪婪的渴求、嫉妒的眼光、愛意的蔓延、憎恨的情緒、奇特的渴望,以及如鬼魅般抑或是現實中的敵人們,那我與之持續搏鬥的回憶戰場——願它們永不賜我寧靜。」無庸置疑,即使是在同志的書寫已經遍地開花的當代,若海史密斯健在,她的作品依舊會持續保有爭議性,因為她對於人性能經驗的情感範疇的探索,毫不妥協,也不畏懼。